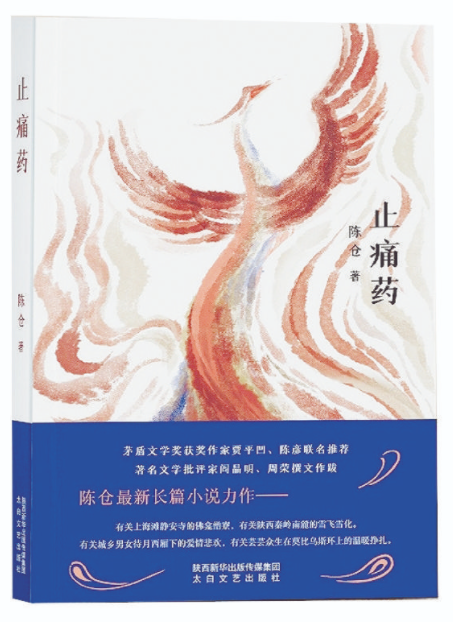
陈仓的小说具有强烈的自叙传色彩,这也让人从中可以感受到某种天然的信任:故事的真实和情感的真挚。《止痛药》说的是一个以陕南农民身份进入上海的青年,却与这座城市产生了紧密的联系,从此无法离开。小说以章节交替的形式,让发生在上海和陕西丹凤大庙村两个地方的故事交错呈现。
小说里的主人公陈小元闯入上海并非偶然,他不是因为谋生打工才来到这里,上海是他在乡村土炕上就梦想过的地方。陈小元一睁眼就与这座城市的代表性人物相遇,他被一个事后才知道叫凤姐的人一脚踢醒,而这位凤姐是地道的上海人。陈小元在懵懂的交流中,无意掉入了命运的漩涡,从此无力自拔。
陈小元这个在大庙村打棺材的木匠,与凤姐之间的差距根本不需要分析,但他最大的优势就是不怕别人嘲笑,始终坚持自己的梦想,内心坦坦荡荡。在上海与大庙村之间,陈仓搭建了一个极不稳定的平台,设置了一种极其危险的关系。我想起陈仓的同乡贾平凹长篇小说《秦腔》中,引生深爱着“村花”白雪,然而这是一份毫无希望的单向苦恋,在冰冷的现实面前,纯粹的爱情不可能是止痛药,反而是撒在伤口上的盐。白雪最后嫁给了在省城里有公职身份的同乡夏风,即使对后者并无感情,但二人的匹配度决定了他们生活的稳定性。
《止痛药》里的陈小元和凤姐完全不在同一片天空下,然而怕的就是一个人有了梦想且不顾一切去追逐,陈小元便是如此。梦想是一种意念,它不切实际却又异常执着,所以注定不可能与时代同步变化,有时会显出概念化、“陈旧性”的特点。比如在陈小元和凤姐之间,导致他们不能在一起的阻力不是“白天鹅”鄙视穷小子,而是凤姐的母亲——一个典型的上海老太太横在他们中间,让二人永远无法走在一起。
凤姐的母亲显然是个概念化的人物,她只起到一个作用,就是把凤姐推向一个瑞士人,再把陈小元从凤姐的身边棒喝打走,这就注定了凤姐不可避免的悲剧:她不可能与那个瑞士人结婚,也不可能和陈小元走到一起。凤姐虽然看上去是个光鲜漂亮的知性女子,事实上却是一位完全受母亲管制的不幸女性。陈仓依据从前的想象,表达的是早已萌生的梦想,他对这种梦想必然要破碎早有自己的认定,于是就在描绘美好梦想的同时,又极力地用自己的笔拆毁它,只有这样才可能满足某种平衡。
这种平衡更集中地体现在陈小元的命运结局上,一方面他居然像中世纪的爱情追逐者一样,经历了仓皇跳窗而逃导致终身残疾的惨剧;另一方面,他又似真似假地成了凤姐女儿的父亲,最后他就带着这种巨大的创伤和意外的“收获”重返大庙村。小说展开了一个极不平衡的双重世界,从中我们读到了凤姐对陈小元缺乏依据却也因此更显纯粹的爱情,陈小元即使终身残疾也无怨无悔的执着,包括他对上海毫无怨言的眷恋。女儿凤妹不仅让他享受了亲情,而且也让他和上海有了不可剥离的关系,他在痛苦中满足着。
读陈仓的小说,有时会让人想到郁达夫、庐隐等人小说里塑造的“烦闷”的“零余者”形象,特别单纯却又异常坚定。在《止痛药》里,陈仓始终把陈小元塑造成一个乐观面对痛苦,朝着梦想跋涉的有志青年。陈小元为自己获得的每一点进步而兴奋,不因为屡受挫折而迁怒于任何人,他相信爱的力量,相信人生痛苦可以通过爱得以缓解甚至治愈,并始终坚信爱是最好的“止痛药”。这是多么善良的愿望,而且“这理想之花就盛开在现实的土壤中”。
我曾经认为,贾平凹《秦腔》里败落的爱情因为引生彻底的善良而得到弥补,这种以善作为爱情失败的补偿,也是很多中国小说家自觉的选择。在陈仓这里我仍然读出了这一点,他为自己笔下人物开出的治愈痛苦的药方依然是爱——因为他笔下那些带有自叙传色彩的人物所理解的爱,从一开始就包含极其深厚的善的元素,爱与善本来就融为一体,从未分开。(阎晶明)
(责任编辑:卢相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