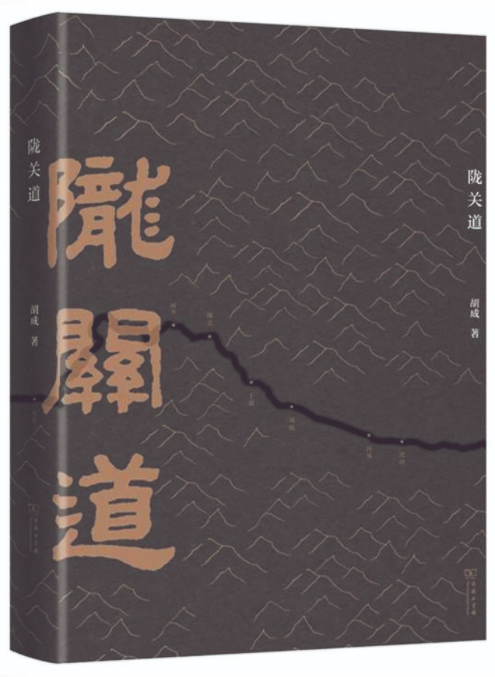
孙群萃
《陇关道》是一部关于丝绸之路的游记。提及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人们常常有这样的偏执:只有进入河西走廊后,才算到了真正的丝绸之路。其实,西出长安不久便会遇到第一重屏障——陇山。对于这座山,胡成在《陇关道》里曾这样形容:“秦人西去,陇山是迢迢万里路的第一道惊悸。不只因‘其坂九回,不知高几里,欲上者七日乃越’的险峻,更有从此家国难归的凄惶。”
古人在陇山探索出两条路:一条是沿着泾水河谷的萧关道,一条是先走渭水、再溯汧水的陇关道。萧关道在北,俗称“北道”;陇关道在南,俗称“南道”。唐亡以后,随着传统丝路的衰落,陇山也渐渐淡出文人的视野,《陇关道》讲的正是这处丝路古道上的人和事。“我对历史的兴趣,由盛唐降至晚清,足下仍是丝绸古道,眼见得却是衰草斜阳。”胡成在《作者手记》中这样说。
一位优秀的游记作者应当熟识地理,并充满实地踏勘的勇气。没有对自然山川通彻的认知,地理空间与心灵空间撞击后产生的感受便无法传递给读者。“他出陇州,我入陇县。”这句话虽短,但空间感极强且信息量巨大。一“出”一“入”,相隔两个多世纪,而地名也由“陇州”变为了“陇县”。
一部厚重的游记缺不了“史”。除了对历史事件的铺陈,《陇关道》也具备宏大的历史感。“八百里秦川,中国最伟大的一片沃野,秦汉隋唐肇兴于此,是我们最初的荣耀之地。”这一句写得极其恢宏,只三十三个字,就道出了关中地区在中国人精神世界中的地位。
一部温暖的游记少不了对历史的同情心。督抚陕西的毕沅曾对辖区内重要历史遗迹立碑为记,然而其中部分却被认为有张冠李戴之嫌。胡成是这样理解这种时代局限的:“记录却是客观的。如果所记之处还在那里,我们可以再去细考;如果已经湮灭,我们起码还能知道,这里曾有一冠,那里曾有一鹿。”
一部扎实的游记需要通过具体的“物”去承载历史。对于所描绘的历史与地理空间来说,这个“物”不仅是一个能够从容收纳人物、历史的容器,也是所在城市的脊梁,如《西安》一文中的碑林。就碑林而言,它为我们提供的精神慰藉是西安这座城市所独有的。碑林外,沿城根儿坐下,要上两个馍,掰好,吩咐老板煮来。这一头空气里弥散着葫芦头特有的香气,那一旁的朱门内藏着千年国本。猪大肠与古碑、酒香与墨香、大俗与大雅,仿佛就是历史在这座城市里的缩影。一座城市有了这样的“物”,便永远都是健朗的。
《陇关道》中描写的人物众多,既有封疆大吏、学者、军人,亦有史书向来疏于记录的布衣黔首。胡成对湮灭在历史中的小人物充满了悲悯之情,他在《西安》中讲述了金圣寺的毁灭,之后便感慨死于战火的团总石仓:“如果不是这场战争,未到古稀之年的石仓,或许正坐在香火仍旺的金圣寺山门外,袖着手,眯着眼,看着陶家的车马缓缓走过。”文中的陶家车马里坐着的是三十年后随父入疆的陶保廉,他为我们留下了一部“切于身心家国”的《辛卯侍行记》。而与之并重的《河海昆仑录》则是更率性的游记,提及碑林,这位进士出身的谪官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凡余四十年来目见梦想诸名碑,咸在其中,得手模而遍读之,真人生快事。”
我们向来不缺乏宏伟的历史叙事,但疏于关怀心灵的细节。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六月,莱阳人赵文耀在幽暗的石壁上写下了“因题洞壁,以志岁月”的题记。公元2020年,胡成用这本《陇关道》完成了他的“以志岁月”。几十年、数百年后,若有人再次关注起这条贯通关陇的古道,第一个想到的或许就是这本书。在书中,行、站、坐、卧的是陇山两侧那些有名有姓、有父有母、知冷知热的众生。
(责任编辑:卢相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