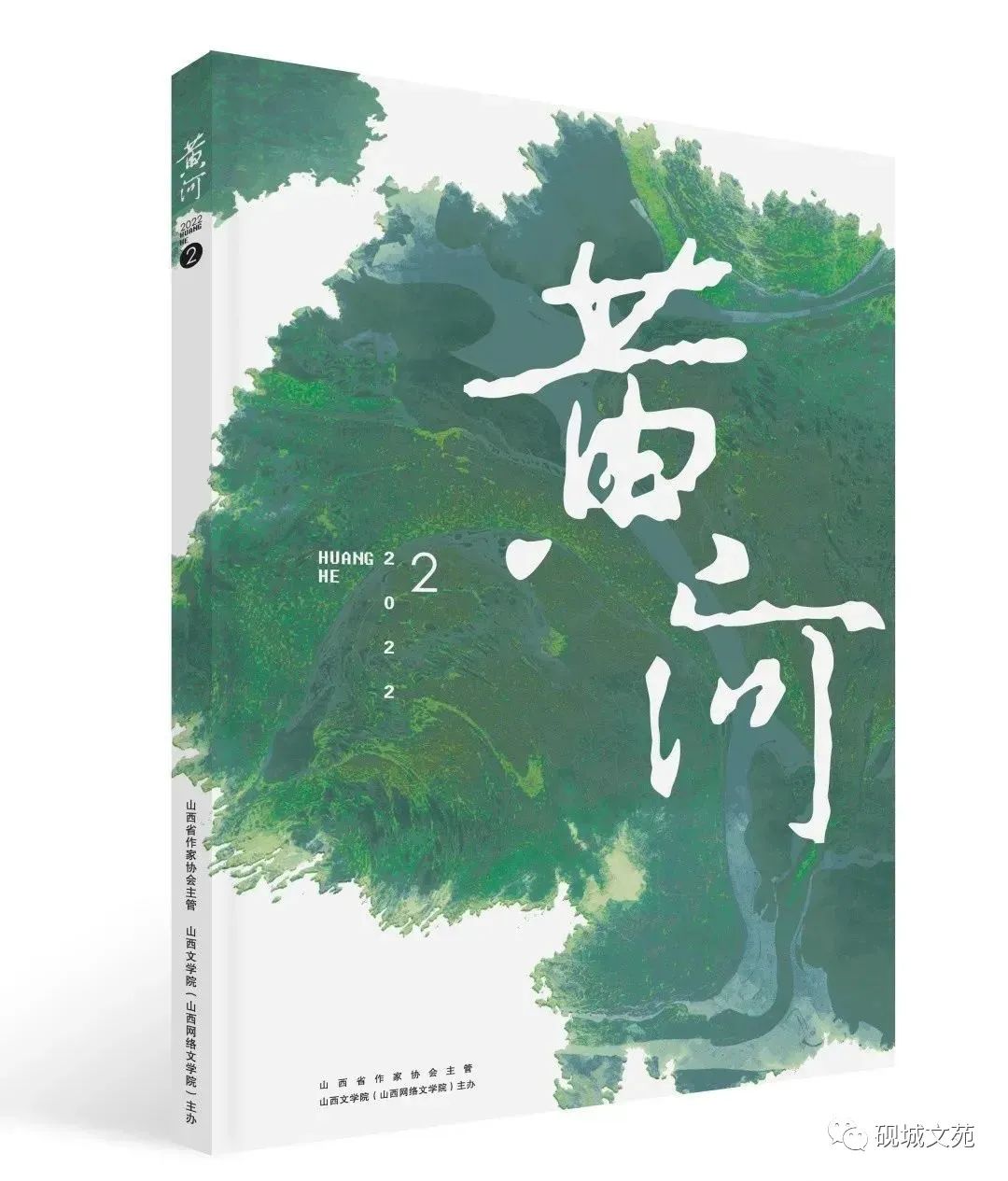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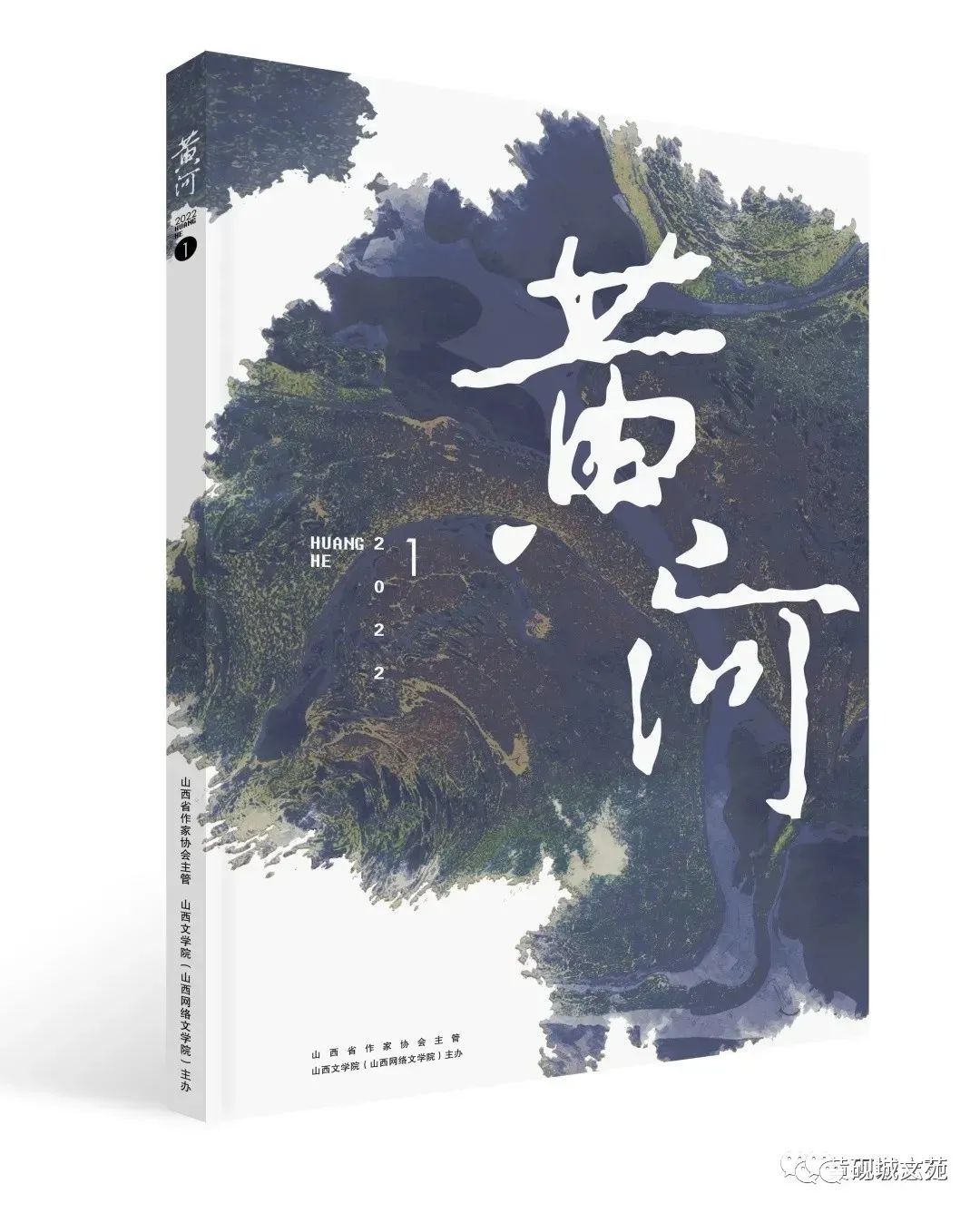
本文原载于《黄河》文学杂志2022年第1期和2022年第2期。
前 言
1977年,我国高考制度的恢复,改变了成千上万中国青年的命运,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几十年来,我见过了太多的人在为1977年的高考而慷慨激昂、口若悬河、奋笔疾书,但从未见过有谁站起来为1977年的中专考试说上一点什么或写上一点什么。
事实上,1977年我国的中专考试和高考是同时并立于改革潮头的,他们如同一对同卵双生的兄弟,同时呱呱坠地,同时健康成长!
如果说,高考制度的恢复改变了好多青年人的命运,那么中专考试制度的恢复则一定是改变了好多好多青年人的命运。
冬去了,春来了,花开了。经受了严寒折磨的人们,脸上顿时绽放出了如花儿一样美丽的笑容。
积累了整整十年的浩浩荡荡的考试大军,同时走进了全国各地的考场,其场面之壮观、影响之深远,世所罕见。
能够成为这浩浩荡荡队伍中的一员,我三生有幸。
那年冬天,在那个突如其来的考试面前,我很是手忙脚乱了一阵子。先报了中专,又改成大学,最后又改回了中专。
因此,我成为了一名中专生。并永远地定格在了这一庞大的但并不像高考那样光彩照人的中专生队伍中间。
但,我的名字似乎还是被当地一些考生给记住了。
于是,就不断有人对我说,像你这成绩,在全县名列前茅,若要报上大学,定然会实现更加华丽的转身。
当时,我也坚定地认为,我把一次更加华丽转身的机会给错过去了。
我也曾为这一似乎优柔寡断的选择,而悔恨了好多年,包括做梦也在叹息。
后来,我想尽办法来弥补。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文凭搞下一大摞。与之相随,履历表上的学历也在蹭蹭蹭地往上蹿:中专、大专、大学。而且都是牌子很硬的那一种。
再后来,研究生的学历也差不多到手了,我突然停住,问了问自己的内心:搞这些学历有啥用呢?回答说啥用都没有!简直如同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原来我的内心深处只承认我是一名中专生,而拒绝其它任何学历。
于是,我把这种所谓的后续学历以及它给我带来的种种虚荣彻底地扔一边去了!
退休后,愈发觉得没意思,愈发觉得碍眼,于是只用了一根火柴,就将那一堆十年辛苦不寻常所换来的东西化作了一股袅袅清烟,轻轻的,让她飞走了!
细细想来,那个中专文凭,倒是实实在在,虽然有点低级,但她却是我安身立命的根基。是它的一路引领,让我从农村走到城市,从农民变为市民,实现了我人生的蜕变。其余的文凭,虽然光鲜亮丽,可曾给过了我些什么?
像糟糠之妻那样,虽然相貌平平,未曾引起我的心动,更谈不上什么死去活来的炽爱,但她善良贤惠,忍辱负重,任劳任怨,给了我家庭、给了我儿女、给了我几乎所需要的一切。我还能有啥说的?我们必须不离不弃,相伴永远!
履历表上,过去出身一栏填成分,后来出身一栏填学生。过去我的出身是中农(文革时期村上硬给提拔成了上中农),后来我的出身是中专。
中国,中庸,中农,中专,加之我上有哥哥姐姐,下有弟弟妹妹,也处于中间位置,我相信我的命离不开一个中字!
爱因斯坦说过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想,此话如果成立,那么世界上的所有事物,既有其共同的运行方向,又有其各自该去的地方。
人,不管心上曾经有过多少痛点,但我们必须尊重当初自己的选择!必须尊重自己的行走轨迹!
一
1977年秋分一过,晋西北的天气明显转凉。
我记得,我们还在地里刨山药、场上打谷子,五寨县就召开了冬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简称农水建设)大会战的动员大会。
应该说,正值秋收大忙季节,就着着急急上马冬季大规模的农水建设,多少还是偏早了一些。可在那个年代,凡事都讲究一个早字。早计划、早安排、早动员、早部署、早行动、早落实、早检查,早督促、早评比、早总结,几乎成为办一切事情的思维定势和工作套路。
名为冬季农水建设,但实际上却占去了整整半个秋天。这一挤占,势必会打乱正常的农事活动。
县上的动员大会刚刚开过,各公社就迅速进行贯彻落实。
山道弯公社位于五寨县的西北端,与河曲交界,距离县城100多里,是全县最偏远的一个地方。公社书记、主任、武装部长一行八人,开完会找了个手扶拖拉机就打道回府,可等回到公社,已是晚上七点多了。
为了做到“贯彻上级精神不过夜,” 他们不顾车马劳顿,又连夜召开了各村的领导干部会议。
第二天,各村各队照葫芦画瓢,再层层开会,贯彻落实县上和公社的会议精神。
其实,照葫芦画瓢只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就一般情况而言,越是上面的会议越是复杂越是抽象,越是下面的会议越是简单越是具体。
等会开到村上队上,什么目的意义、方法步骤、工作重点、工作要求之类花里胡哨的东西一概没人讲了,开会的核心只剩下一个,那就是出多少人,出多少钱,出多少粮,以及如何来出?实质上就是研究解决“一平二调”中无偿调拨的问题。
出钱出粮倒不在话下,都由大队统一解决,可出人就没那么简单了,因为它会冲击到好多个家庭正常的生活秩序。
那时候,村里每年都要派出一部分强壮劳力参加县上或公社组织的修路、修坝、修渠等项工程建设。社员们都知道,这种外派人员,除了受苦受罪以外,别的好处啥也没有,在村里挣多少工,出去还是挣多少工。又且,自己出去了,家里的营生就没法子周转了。比如,我们村子的人畜吃水,一般都得由大男人们起早贪黑到二里多远的深沟里去挑,你要是走了,这任务让谁来完成?这还仅是一种,柴米油盐酱醋茶,烧火做饭扫院落,撵鸡放羊喂牲口,担土垫圈搂圪渣,营生多着呢,样样都得有人去做。
事实上,越具体的事越缠手。有时候县上和公社的领导靠红口白牙的大话空话套话就可以把日子糊弄过去,而到了农村,想要见了矛盾绕道走,真没那买卖。谁都知道,村干部的行事风格多半都有几分霸道和几分蛮横,其实,说句实话,那全是被逼出来的。
我一直认为,这个世上最难当的官儿,不是省长,不是市长,不是县长,而是农村的生产队长。

那年,五寨县冬季农水建设大会战的主要任务是修建从南峰公社到三岔公社长达30公里灌区内以土石为基础、混凝土为沟槽的主干渠。就工程规模而言,这是建国以来,五寨县继南峰水库主体工程之后,举全县之力修建的又一大配套性的水利工程。
如此浩大的工程,计划抽调6000个民工,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在两个冬天完成。难度可想而知。
当然,这项工程建成后,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它不仅可以充分利用南峰水库的丰厚蓄水,解决五寨县八十里丁字平川数十万亩耕地的灌溉问题,还可以解决一部分村子的人畜吃水问题。
应该说,它与那些纯粹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还是有着本质的不同,它虽然也打上了强烈的时代烙印,但绝对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民心工程。
为了把这项工程抓紧抓好抓实,按照当时的说法是,既要轰轰烈烈,又要扎扎实实,县革命委员会专门成立了冬季农水建设大会战的指挥部。
指挥部设在灌区北中段位置的新寨公社所在地。指挥部的总指挥自不必说是由县革委员会的一把手亲自担任,副总指挥由县革委员会的常委共同担任,指挥部其他成员则一律由县直部门和各公社的主要领导担任。在此基础上,指挥部又下设了若干个工程小组,可谓门类齐全,结构严谨。
如此强有力的指挥系统,调度和控制全县各类建设资源,其权威性无容置疑。
在动员大会开过以后,全县上下雷厉风行,不舍昼夜地抓紧准备,谁有困难谁克服,谁有问题谁解决,矛盾绝不允许上交。到第七天头上,所有的人财物都全部到达了指定位置。
这次农水建设,还有一个特点是,全部采用了军事化的管理模式。每个村子为一排,每个公社为一连,全县十八个公社十八路人马组成一个团。当然,排里面还有班呀组呀什么的,从大到小,一应俱全,完全套用了部队上的组织建制。团长由县革委主要领导担任,连长、排长以此类推由公社和村子里的主要领导担任。
因此指挥部就又有了一个雷霆万钧的名字,叫五寨县冬季农水建设作战团。典型的一套人马两个牌子。
我们知道,军队在作战之前,一定会有一个干脆利落的作战命令。
这次冬季农水建设大会战也是如此,在全县的动员大会上就将各路人马的工作任务讲了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随后层层传达会议精神,实质上是层层分解会战任务。而且,为了保证所下达的任务不打折扣,还层层签订了军令状。
大会战六千名民工的主要任务是采掘和运输工程所需各种类型的建筑材料。至于大渠的垒砌施工,则是另外一回事情了,因为它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只能由县上的专业队来完成。
工程所需材料主要包含土、石、沙、水泥四种。而在四种材料中,除了水泥由县上统一解决外,其它三种材料的供给都分解到了各个连队和基层单位。
实事求是地讲,这些材料采掘和运输的难易程度还是有着天壤之别的。比如,土可以就地取材,到任何一个地势较高的土丘或山角下都可以挖取,以不损坏耕地为原则。而沙子就相对要难些,得到地势比较低的河槽里去挖,路程虽不算太远,但拉着沙子需一路上坡,又且路基松软,费力费苦自不必说。最艰难的应该是石材,一律得到五寨和偏关交界处有一个叫云梯峁的石山上炸取,不仅风险大,而且运距远,动辄就是几十里。
那时生产力极其低下,根本没有什么机械化作业一说,一切材料的采集、装卸和运输都得依靠人力和畜力来完成,我们在工地上所能够见到的最先进的生产工具莫过于毛驴拉着的小平车了。
我们山道弯连队便是一个典型的赶着毛驴拉着小平车的连队。
我们安营扎寨的村子是离指挥部仅有几里路的旧寨大队,我们所承担的任务是从旧寨附近的河槽里往灌区上拉沙子。因为拉沙子太费力气,只靠人力无法完成,那就得凭借最先进的生产工具了。
话分两头。再折回来说一下我们村子为本次农水建设大会战抽调人马的事儿。
其实,不是抽调人马,准确地说应该是抽调人驴。因为山道弯公社给我们村分配了八辆驴拉小平车的任务。其实很好计算,有一辆小平车,就需要有一个拉平车的驴,也就需要一个赶平车的人。这样车、人、驴才会协调配套起来。另外到了旧寨,人需要吃喝,驴也需要吃喝,这样就需要另加一个担水做饭和喂牲口的,如此算下来,一共是八辆平车、八个驴、九个人。
那天,我们村子先召开村干部会议,再召开群众大会。村干部会议的任务是商定抽哪些人、哪些驴、哪些平车的事儿。群众大会的任务主要是宣布村干部会议的有关决定,并做好有针对性的宣传和解释工作。
因为我是村子里的团支部书记,虽不是什么重要的角色,但诸如此类的干部会议则是不可或缺的。
因为是秋收大忙季节,所以村子里开会也非常讲究效率,能一句话说清楚的,绝不会用第二句话。当人到齐以后,支部书记开门见山说明了要研究的事项,然后请大家发言。
只见支部委员文亮爷爷说道,军令如山倒,要人给人,要驴给驴,要啥给啥就是了,这没啥好商量的。
支部书记赶快打断文亮爷爷的话说道,要啥给啥,理是这么个理。驴好办,挑八头口小能干活的驴就行。平车子也好说,把库房里的平车子挑出八辆来,让三木匠小修小补拾掇一下就能使用。可是抽人就得动动脑子了,得看谁听话,看谁实在,看谁做营生利索,千万不要给咱考虑那些油嘴滑舌,投机取巧,只能瞅旮旯,不能下苦力的三等社员。这些人派出去给咱丢人现眼哩。
文亮爷爷接过话来说道,不是给咱丢人现眼哩,而是这种人根本就派不动。他们又懒又馋,又能使坏,活儿干不好,歪理邪说还一套一套的,要是把他们定上了,接下来怎么办?社员大会还怎么开?让他们一叫唤,一顶撞,一圪搅,看样学样,狼碰开门狗也跑进来,其他人也派不动了。
只见大队长世德爷爷把小蓝花烟锅子用劲抽了几口,然后胸有成竹地说道,不用绕弯子了,我来提名字吧。提出来,大家看合适不,合适就定下来,不合适就另外寻人。当然像你们说的那几个鬼见愁,我肯定不会提出来。
其实,世德爷爷和支书的关系谁都清楚。他俩不仅是本家叔侄,而且工作上配合得也颇为默契。他俩经常会在会上一唱一和演双簧,一个拉弓一个射箭,一个扮黑脸一个扮红脸。惹人的事多半由世德爷爷出面,讨好人的事打圆场的事多半由他的侄儿子支书来出面。问题是世德爷爷,乐此不疲,一辈子都是这样,甘愿屈人之下,但从不计较什么干锅油气。
说来也怪,按说世德爷爷一辈子当干部,尽做傻事,尽被人利用,该是把村子里的人得罪遍了,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世德爷爷不仅没有得罪下人,反倒落下了一摊子好名声,人们说他心直口快,有杀有放,不斗心眼,胸怀坦荡,是一名真正能够驾驭了复杂局面的好干部。即便有些事做得过分了,那也是受人指使,与他的本意无关。
也真是,如果在群众中没有一定的威望,怎么能在领导岗位上一干就是三十几年?
父亲说,你世德爷爷看上去傻不拉几,实际上比谁都精明。我也这么认为。
会上,世德爷爷提出一连串名字供大家讨论,大家稍一斟酌,觉得无可挑剔,很快就将八个外派人员定了下来。仔细一想,世德爷爷真是良苦用心,所提八个人员,皆为清一色的老实圪垯,没有一个扎牙货。
不过,最后还是有一个人选把会议给卡住了,那就是谁去带这个队?现在兵齐了,短一个带兵的人,而这个带兵的人只能从在座的这些村干部里边产生,大家大眼瞪着小眼。
这个人选,世德爷爷并不曾提议。
按说上面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带队之人必须是村里的主要领导。谁都清楚,主要领导指的是谁。可支部书记说他家里有困难去不成,主任说他身体有毛病去不成,再挨个儿往下说,不是这困难就是那问题,眼当对鼻子,自己不想去又不好提议别人去。因为大家都清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最普通的道理。
会议僵在那里,静静地,一动不动,世德爷爷也靠在桌子上,微闭起小眼睛,一个劲地拿着烟袋吞云吐雾。

最后,还是文亮爷爷打破了会场的沉闷气氛,他说,你们谁也不想去,这困难那问题,明摆着,出去会受罪,不如守家在地舒坦。现在支委成员里只有生产队长和我没说话。生产队长世德老汉,自然不能走,走了谁来吼吼喊喊抓生产?我已经是年近六旬的人了,让我去带队,大家于心何忍?如此这般,那也就是说,七个支委谁都不能挂这个帅了。那该怎么办?剩下的人,这不是,就这两位了,一位团支书,一位妇联主任。妇联主任有孩子,肯定不能考虑。那么还有谁呢?磨眼子里放屁——没推头了,好歹就是团支书的买卖了。
文亮爷爷说到此处,大家齐刷刷地把眼光扫射到了我的身上,我顿时有了一种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感觉。
而后,只见世德爷爷啪啪啪把烟锅头子在地砖上搕打了几下,转过脸来笑眯眯地对着我说道,这倒也是个办法,钟生,你看能不能去?
我略微迟疑了一下回话道,世德爷爷,文亮爷爷,二位都是我非常尊敬的爷爷,你们让我去,肯定是看得起我来;你们问我能不能去,我作为小辈,哪里能说顶脸面的话。可是请二位爷爷想一想,我仅是个村子里不上席面的一个小毛卒卒,离主要领导七帽子八远,八杆子打不着边。俗话说坐板凳称身份,我怎么能自不量力,给个杆杆就顺着往上爬呢?
此时,会场上出现了一阵很是短暂的笑声。
紧接着,大家就围绕我能不能去带队这个话题议论开了,有和我观点相同的,有和我观点相左的,也有模棱两可的,始终难以达成一致。
见会议再度陷入僵局,世德爷爷不失时机地又扮开了黑脸,但今天的唱词似乎出奇地新颖。他不紧不慢地对着我说,钟生,你说的也很有道理,团支书确实是离主要领导的位置远了一些,但你年轻,有后劲,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前途大着哩。年轻人进步,既得靠组织培养,又得靠自己努力。钟生,你也不要谦虚,该上就上,千万不要错过了这八辈子都等不来的机会。
世德爷爷说话向来很直,但今天却一反常态,搞了一个很大的弯弯绕。表面上看无懈可击,可明眼人都知道,他是在忽悠我。什么八九点钟的太阳,什么前途远大,什么组织培养,什么该上就上,纯粹是言不由衷。你想,真正要是一次八辈子都等不来的好机会,怎么会遭到所有村干部的推缷、抵触和冷落?怎么还会轮到在家族对立中经常为主要领导重点设防的一个年轻人头上?
说实在的,世德爷爷的这些话,让我内心十分反感。明明是个苦差事,你们谁都不想去,捉我个大头鳖也就算了,为何还要把这个苦差事硬加码成八辈子都等不来的好机会?我又不是个二百五,被你们卖了,再帮你们数钱,真是的!
我们的支部书记向来以能沉得住气而名闻乡里。他看下事情到了瓜熟蒂落的地步,才站起来伸了伸懒腰,慢条斯理地开始拍板定案。他说,我完全赞同大家的意见,支委们各有各的困难,我很理解。即便你们要去,我也会横竖把你们拦住。由我们团支书带队,既是一个无奈之举,也是一个聪明的选择。团支书,年纪轻,有文化,一贯踏实能干,也是支部的重点培养对象,出去锻炼锻炼,只有好处没有赖处。当然,在带队这件事上,咱们村子的情况特殊,我还会尽快给公社领导做个专题汇报。说到此处,他又转过头来对着我说,希望你出去把队伍带好,保质保量完成大会战交给的任务。然后还笑容满面地问我,钟生,你还有啥要说的?包括你的困难。
我非常清楚,支部书记更是在那里演戏,他的演技那绝对是炉火纯青,评个全国的梅花奖也应该是绰绰有余。
五荣叔曾经有个惊人的发现,他说:村子里的会议,每有难以派遣的营生,总会开启“苶球谝山汉”的模式。
谁是苶球?谁是山汉?这次会议究竟是不是苶球谝山汉?因为拿捏不准,我也不敢妄断。
我冷静一想,这个带队的差事既然不可避免地落到了我的头上,与其叫苦不迭,还不如顺坡下驴也来几句漂亮的话,这样既可表明自己的胸怀,又可保全大家的体面。
于是我稍微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思绪,然后颇为高调地回支书的话:“请支书放心,请支委们放心,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村子里的主要领导,但我知道组织性纪律性是怎回事情。既然大家信得过我,让我扮演这个重要的角色,那我就顺着杆杆往上爬一次。用你们的话说,就是不要谦虚了,该上就上,抓住这个八辈子都等不来的机会,去磨砺自己。这当然是大家的一片好心,一片苦心,我感谢各位。可是,在我看来,这个世界上,不论好事赖事,大事小事,难事易事,都得有人去做。你不做谁做,你不干谁干?不用说这是一次农水建设的大会战了,即便是真的起了战事,拉我们上前线,去堵枪眼什么的,那又能怎么样?我们的前辈,不都是这样子走过来的?在座的文亮爷爷,南征北战,英勇杀敌,献出了宝贵的青春,落下了个二等伤残,回村后不居功不自傲,仍然在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你说,我们年轻人在组织需要我们的时候,有什么理由跳出来讲价钱、讲条件、讲困难……”
听了我的表态,大家一个劲地夸我够个大男人够个大丈夫。我当然清楚,此时他们的内心,个个都充满了成功的喜悦。
就这样,我率领着村子里的八辆平车的辎重车马,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农水建设大会战之中。

徐茂斌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书法家协会会员、赵树理文学奖获得者。原忻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忻州市文化局局长。著有《山道弯弯》《徐万族人》《黄河岸边的歌王》(合著)等文学作品。《黄河岸边的歌王》被收入《中国新世纪写实文学经典》(2000——2014珍藏版)。
(责任编辑:卢相汀)